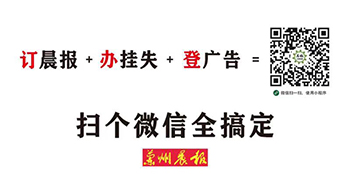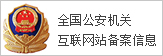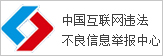□马步升
是的,我是一个不回老家的人,一个生活在距离老家并不算远,而且也并没有忙到分身无术境况的人,几年,十年,二十年,未曾回过一次老家。在我们这个把老家捧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氛围下,非但不容易被理解,相反,对于人们,有关的,完全无关的人们,从各个不同角度的指责,你都得默默听着,默默承受着。因为指责你的人是占据着前定的道德制高点的,而对你开展的合法性指责,对于指责者来说,至少有两层立竿见影的好处,一是满足了自己对道德感的追求,一是可以遮盖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某种不足。国人向来喜欢指责别人,其动机,其功用,大抵如此。谁见过真正有道德的人,会动不动抡起道德的大棒打人?古人说,小人无错,君子常过。说的是小人永远不觉得有错,错了的只能是别人,而君子因为习惯于反省,反躬自问,便常常会发现自身的诸多不是来。我们且不说小人君子之类的语焉不详的模糊话,在日常生活中,小人说出的话往往一派君子气象,大言炎炎,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君子说话往往带有小人腔,因为要求实求真,说话要接地气,而地上有肥田茂草,也少不了污泥浊水。
我并不是没有回过老家。这期间,有几次,站在河对岸的山畔上,在对老家久久伫望过后,决然返身而去,并未像在老家生活时那样——如果从老家以东的方向回家,到了河边,无论春夏秋冬,水涨水落水清水浊,脱掉鞋子,或挽起裤脚,或扒光衣服,趟过河去,那就是家啊——可我再也不愿意趟过这条河,踏上那座被河水和黄土高坡环抱的小村庄了。我不是刻意要这样诀别老家,而是心中不愿,确实不愿,不愿再踏上那片曾经寄托过我十六年生命的土地。但我得郑重声明:我与老家没有任何过节,也与自己的人生处境毫无关系。我与老家的离心离德产生于老家。在我懵懂记事时,有朝一日逃离这个地方,便是我对人生最大的奢望。逃离了,便是逃离了,谁见过脱网的鱼儿会主动返回网里?家是由一个单字组成的语词语义完全闭合的丝毫不具备开放性的概念,在家的前面加上任何限定词或修饰词,比如老家,娘家,便意味着那是别人的家,不再是自己的家了。家只是家,自己的家,生存意义上的家,事实意义上的家,法律意义上的家。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那样醉心于流浪,从能够记事起,这个念头便无比强烈。记事以前呢?我想一个贯穿数十年的念头,和由念头凝聚而起的决心,其诞生绝非毫无征兆。那么,将其归结为天性,将其说成是生命中本身潜藏着流浪的因子,也是在理的。
现在我得说说我老家的样子。
从我记事起,我仰首面前的山,我对眼中能够看见的东西,看一眼后,便不再感兴趣,装满眼睛的渴望是被山挡住的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前面的山以外的事物,便回首身后的山,而身后的山几乎压在我的头上,没有足够的角度观测。严格地说,身后的山并非看见,而是感知到的,那种碾压式的推搡和紧逼,使我时时感到,我会被身后的山推入面前的马莲河中。当然,我后来知道了,身前身后的山,都不是山。这是我终于有足够的体力和自由爬上山顶后才得知的。那是一种叫塬的地形。本来也是可以被称作原的,平原的原,高原的原,原野的原。这是高原上的平地,又是黄土高原上的平地,原来大约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平地,只因是用黄土堆积而成的,质地太过疏松,在雨水亿万斯年的冲刷中,平地被反复切割,如同一个顽童,用刀子、木棍,或手指,在一只蛋糕上,充满恶意地、反复地划拉,而留下的残迹。于是,原变成塬了,特指的含义是:黄土残塬。
而我住在川里。川,便是被洪水切割下去的壕沟,宽大的叫川,窄小的叫沟。细分的话,还有冲沟、毛沟等。本地人对这种地形不会感到惊奇,住在川里或沟里的人,将住在塬上的人,统一称为塬上人,而塬上人则将住在川里或沟里的人,称作川里人。这样的称呼极其厚道,或者圆滑,乃至于虚荣。而这正是家乡民间文化的基本底色:厚道,圆滑,或者虚荣。塬是有大小之分的,最大的塬,比如董志塬,那可是地球上最大的、土层最为深厚的黄土塬,几十万人在这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大约还有几十万座坟头占据着可观的肥田沃土。可喜的是,我出生在董志塬边的马莲河畔,可恨的是,这只是地质学上的说法,要化为真实的人生,还得爬上漫长而崎岖陡峻的黄土高坡,在田园时代,那可是需要卓越的体力耐力才可跨越的一道道天堑啊。一代代男人被这一道道天堑累断了腰,一代代女人被这牢狱一般的天堑禁闭在一孔孔黄土窑洞里,生死荣辱全凭天意,或自己的些许小运气。小一点的塬,可以成为一个县、一个乡镇的核心,而最小的塬,只可供几户人家,或一户人家安身立命,比如,六寸塬、四寸塬。听听这名字!这样的塬,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峁。就是在影视剧中,在摄影绘画作品中常见的,那种馒头样的黄土山丘。明明是峁,却被叫做塬,正是黄土文化的厚道,圆滑,或者虚荣。如同当下将几乎一文不名的人也称作老板,而把脸皮早已山川起伏的女人称作女生一样,都是一种假装。我假装不知道你生存的窘迫,一声貌似恭敬的老板,叫的你也假装自己不那么窘迫了,把身上最后一张纸币掏出来,为的是对得起人家的那一声恭敬,我假装不知道你的实际年龄,一声女生叫出,你也会像那些不谙世事、不懂得人世艰辛,以青葱的肢体语言,以羞涩的神情,决然地,满不在乎的,掏出丰满或干瘪的荷包,买下只有真的女生才可用的物件。
……
而塬上人最喜与川里人联姻。基本的格局大约是,塬上的男人往往讨川里的女子做老婆。川里人在塬上人那里,血液中流转着一种自卑感,川里的女子做了塬上人的老婆,如同民女嫁入豪门,那可是一步登天,人家吃了亏,自己占了大便宜的买卖。这样的选择,处处透着塬上人站得高看得远的高屋建瓴。川里的女子从小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吃得了苦中苦,最容易满足,婆家人偶尔给一个好脸色,都是山珍海味的享受,都是要以牛马般的忠诚和辛劳作为回报的。还有,万一两亲家有什么别扭,最先让步的,理所当然是女方了。塬上的中等男人闲谈间,便可娶到川里的上等女子,塬上的下等男人,哦,得格外声明,这里的上等中等下等之说,与人权概念中的种族无关,说的只是人的先天条件,完全是民间习惯用语。所谓下等男人,指那些家境贫寒,本人游手好闲,家无余财,身无长技,或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体残疾,只要他们格外放下身段,便可轻松娶到川里的中等女子。而塬上的上等男人,那些家有闲钱,人也有说得过去的才貌,门风家风周正,个人没有什么明显坏毛病的人,说一千道一万,是不会把川里的女子放在眼里的,除非你有西施之貌。而荒天荒地的,哪里又会生出西施一般的妙人呢。所以,这只是一种假设。那么,塬上的此类上等男人如何解决婚配呢,第一选择当然是大体门当户对的塬上人家吧。
塬上的女子也有下嫁到川里的可能,无论处于什么情形,都是下嫁。这是老天爷对塬上有些女子天大的不公。不是家境差,严格地说,相对于川里人,塬上没有家境太差的人家,大体平整的土地,一眼可以望出去很远的视野,哪怕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人无一技品无一优,地理环境把这一切的不足都可一把抹平了,就像王侯将相家不成器不成人样的公子,照样可以轻松娶到貌美如花的妻子。塬上的女子相貌再差,差到无盐的分上,川里人都得要当成西施那样仰望。这里说的差,是指那些天生残疾,身体缺这少那,心窍缺这少那,这样的女子在塬上同样不被人看好,哪怕男方比自己还差,男方也不会正眼看你,因为有川里的中等女子早已投怀送抱了。塬上的这类女子,站在塬畔,把川里人俯视够了,扯开嗓门大哭一场,骂天骂地,骂川里人,好似她的不幸是由川里人造成的,然后千挑万选,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最终挑一个家境殷实,门风家风周正,其人老实厚道,勤劳能干的男子嫁过去,而迎娶之前,男方必须给女方家提供一笔让真正的有钱人都得出几身冷汗的彩礼,来报答女方父母给自己养大了一房媳妇。这是纯粹给女方家的,还有给女方本人的,足够八年穿的衣物,足够一辈子用的生活设施,还要规模浩大豪华排场的婚礼。这都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关怀呵护,若不借着这次机会一次备足了,女儿到男方家会受苦的。对男方的一次性搜干榨尽,男方娶一房媳妇,下半辈子基本上都用来偿还结婚债务了,而媳妇除了能够承担传宗接代功能,基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那么,又有心思缜密的人要质疑了:川里的男人干吗不在川里找一个身体大概全乎的川里女人为妻呢?这就不大容易说明白了,非要说就得语涉玄虚,比如人性的弱点什么的,虚荣,攀高枝,攀龙附凤,如此等等,要的是人前的面子,要的是挂在人们嘴上的说头。“谁家谁家给儿子娶了一房塬上的媳妇!”听听啊!修习过史学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最容易忽视细节的学问,在结果那里,动机、过程,往往会遭到有意或无意的遮蔽,而川里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史学了,可史学也并非一味地高高在上,相反,向来与人情道理纠缠不清,而所谓的人情道理的形成,史学无休无止地训育,则功不可没。就像一位乡邻女孩,使尽黄土高坡文化熏陶磨炼出来的坚忍不拔精神,嫁给了老外,而那个老外在那个生活水平与我们还有一定距离的国度里,仍属平民阶层,但人们并不刻意根究这些,舆论一律地说:谁家谁家的女娃嫁给了外国人,看看人家!女孩的家人在人面前从此有了面子,如同结了皇亲。而摆在川里男人面前最残酷的现实是,川里稍微看得过眼的女孩谁又会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川里男人呢。
当然,老天爷关闭一道门,总会随手打开一扇窗的,世界的失衡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但严重失衡,则会导致倾覆。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这种结局也非老天爷本意。道理很简单,受到众人抬举供奉的老天爷,才成其为老天爷,才活得像个样子,正如皇上,高居龙庭,挥斥万民,才算是皇上,孤家寡人一个,是不是皇上都无所谓。老天爷的平衡术在黄土山乡起到的效用,触目皆是,众所周知。川里人也有自己的优越感,真实的优越性,心里的优越感,都有。拿吃水这件最日常不过的事情说吧。黄土高原缺水,对于此,老天爷都是心知肚明的,土层太厚,地表水留存不住,地下水埋藏太深,要是生长于山青水秀地方的人乍然看见塬上人的日用水,当场吓不死,也得吓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塬上人都备有水窖。什么是水窖,就是收集储存雨水的土窖。土窖的建造是一项非常浩大繁复的工程,先在低洼地挖出一方深坑,再用黄土沿圈夯筑成瓦缸状,撮口,鼓腹,收底,就像当下我们常见的那种营养过剩又慵懒昏聩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这当然不够,黄土无论怎么夯筑,都会渗水的。这就需要红胶泥。黄土高原满目黄土,遍地黄土,可要找到红胶泥,比找到成型成材的石头还难。红胶泥就是红土,黏性大,干燥后,不易渗水。先在空地上圈起一方泥坑,把粗糙的红土颗粒碾压成面粉般细柔的粉末,浇上适量的水,人的力气有限,再强壮的男人都是搅拌不匀称的,得用黄牛。挑选一头最为强壮的犍牛,赶入泥坑,一人牵着缰绳,犍牛在泥坑反复转圈,牛蹄每在泥坑走出一步,如同红军过草地那样艰难。等到一坑红胶泥彻底黏结了,那头最为强壮的犍牛也累瘫了,休息半个月一个月都缓不过劲儿,有的犍牛,这样一场事儿下来,强牛变成弱牛,算是半废了。红胶泥顶替的是水泥的作用,先贴墙箍起一圈,再将泥团搓成胳膊粗细的泥棒,从已经相当致密的泥墙上楔入,像是给木头家具上卯榫。每片手掌大的墙体上楔入一根泥棒,俗称钉窖。一口这样的水窖,如果管护得当,可供几代人使用,谁家拥有这么一口水窖,几乎是最值钱的家当。水窖阴干了,改好水路,遇到下雨,便可蓄水了。
必须是暴雨。黄土层深厚而疏松,小雨,乃至中雨,地面难以形成水流。暴雨来得急,收得也急,地面洪流涌起,沿事先修好的水路灌入水窖,而水路都是黄土路面,洪水如利刃,沿路切削黄土,水路上有什么捎带什么,牲口粪,枯草枯树叶,杂七杂八,一并涌入水窖。刚入窖的雨水,最好不要去看,一窖黄泥汤,上面漂浮着各色杂物。这时候水窖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人不能饮用,牲口也不能饮用,谁用谁拉肚跑稀。必须沉淀几天半个月,泥沙下沉,水色渐渐变为土黄色。取用时,像在水井打水那样,水桶吊下去,拉起一桶土黄色的水。大一些的水窖,可以储水七八十方,在夏季,随用随储,冬天过后,春旱开始,水窖有无水,储水多少,直接关系到日常生活。到夏天暴雨来临之际,水窖也要空了,得赶紧清淤,所谓一窖水半窖泥,窖底淤泥已有一米厚薄了。当然,时代在进步,现在好了点。前多年,有关社会组织在极度缺水的黄土旱塬大规模修建母亲水窖,修造原理与泥窖类似,只是用砖和水泥垒砌窖体,再用水泥修建雨水集流场,这样一来,中雨,乃至小雨,冬雪,只要水泥地面起水,都可汇入水窖,而且,落在水泥地面的雨水杂质较少。这多年,塬上的人看到了这点好处,也不惜工本,几乎家家都有了这种集水设施。说是水质好,只是相对而言,只是依照塬上人先前的饮水标准,在城里人,在川里人那里,饮用未经净化的雨水,仍是一桩可怕的事情。
讲究的人家,也会不惜工本去吃泉水,而泉水只有川里或沟里有。取一趟水,最短距离也要三五里,大多都在七八里,乃至十几里。挑一副空桶,从陡峭的黄土高坡下来,装满泉水,再原路爬坡,取一趟水,往往需要耗费几个小时,半天功夫。这只有强壮男人在农闲时分才可做到。有大牲口的人家,可以赶着毛驴或骡子驮水,妇女、小孩、腿脚灵便的老人,都可以做到,而一对大号的驮桶,一次可以盛水二百斤,抵得上人工取水两趟。水来得不易,用水便格外俭省,塬上人家再不懂得过日子的人,浪费粮食的行为有,浪费水的人绝对没有。川里人挖苦塬上人,往往说,到你家门前讨一口水喝你都不舍得。确实,是夸大了些,要馒头吃,只要有现成的,别说是乡邻,哪怕是要饭的外乡人,一般都不会被拒绝,而要喝水,那可真不一定给你。
人畜饮水是再也日常不过的事情,因其日常,说成是天大的事也不为过。在这一点上,川里人的头颅尽可以抬得高过垂直高度几百米的黄土塬,然后俯视塬上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川里人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在漫长的时代,黄土地带草木稀疏,居民的烧柴主要依靠庄稼收割后的秸秆,还有山坡上的蒿草。但,秸秆的用途太多了,比如大牲口在冬天的干草,而秸秆本身是不经烧的。蒿草便成为主要燃料。人口充分繁衍后,塬上哪怕脚掌大的平地都种了庄稼,哪有野草的生长空间?再说了,蒿草这种植物,夏秋间长高了,极其鲜嫩,连根拔下来,晒干了,烧起来可真烦人,火力不足倒是小事,主要是烟太大,农村都用土灶,塞进去一把,火灭了,却不能用风箱,风箱一起,柴灰轰燃,轰灭了火焰,也将灰雾吹得满灶屋都是。只能用嘴吹,嘴对着灶膛,用力小,扇不起火焰,用力猛,火焰轰然而起时,一股浓烟,一团灰雾也跟着喷薄而出。而这种柴火又是极易熄灭的,吹一口,一道火焰,一股浓烟,一团灰雾,烧火者两包眼泪,一脸灰雾。嘴刚离开,又熄火了。一顿饭做下来,眼泪根儿都被剜出来了。
川里地广人稀,野地多,许多地方,一户人家占据一条冲沟毛沟,或一座小山包,勤快的人家,屋前屋后广植树木,有果树,也有炭薪林,每年剪伐下来的树枝,都可以对付一阵子的。还有,门前河流每年夏季都是要发几场大水的,黄汤滚滚,裹挟着各种杂物,比如,树枝,乱草,牲口粪,等等,要是来自东边子午岭林区的洪水,那就可观了,河水整个都是黑的,大树亦不鲜见。河边的人都有从古以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从河里捞上来的东西,谁捞上来归谁所有,包括活人,主要是青年女子,理所当然归打捞者,假如打捞者家人正好没有婚配需求,则可以当成自家女儿嫁给亲友,而该女也会将自己的救命恩人当成娘家。不说这种属于小概率事件的非常好事了,即以正常而论,一场大水,往往可以解决大半年,乃至几年的燃料。发大水时,每个村子人声鼎沸,一片不分点的吆喝声:捞柴了!老少男女,凡是能够行动的人,扛着铁耙、木叉、舀子等工具,呐喊着,奔向河边,占据有利位置。所谓有利位置,也就是回水湾,或河水拐弯处,中流正好靠近河岸的地带。人们挥舞起各种捞柴工具,将洪流中的漂浮物,划拉到岸边。碰上大树,也正好离岸边稍近,一个人,或一户人家是绝对拉扯不出来的,这时,合作精神便诞生了,几户人家各自水性好的男子进入洪流中,合作拖住大树,在几尺高的泥浪里颠沛起伏,先顺流而下,借着水势,慢慢将大树拖离激流区,在下游的某个回水湾,再拉扯出来。捞柴行动结束后,参与者对大树分解了,然后平分。也有大树太大,水流太急,继续拖扯下去会有危险,一般也不会有人效法中学语文课本上宣传的金训华为了在洪水中抢救电线杆而搭上性命的英雄壮举,此时,有经验的人会大喊一声放手,大家同时放手。人命第一,再值钱的东西原本是洪水冲来的,捞着了归自己,捞不着,还给洪水,没有人会因此拼命的,也不会有人因此心生遗憾。可别小看了洪水中捞出的烧柴,大多都是普通植物,蒿草,秸秆,草根,等等,经洪水浸泡后,晒干,顶得上干树枝用呢。不起烟,火力壮,随便抓起一把塞入灶膛,风箱扯起,火苗呼呼地,一顿饭用不了多少。发一次大水,哪怕洪水发自苍白干旱的黄土区,也会大有收获的。那些漂浮在浪头上的黑乎乎的杂物,碎草,树叶,羊粪之类的,用不着铁耙木叉之类的,用铁网细密的舀子捞上来,晒干了,仍是上好燃料。这种燃料被称之为浪沫子。洪水退后,凹凸不平的河滩上,还会沉淀些许浪沫子,用竹扫帚攒起,拿回家,也是上好燃料。同样的植物为何经过洪水浸泡后,质地坚硬了,烟灰少了?河边的人没有人去管这闲事,好用就行了。其实,原理很简单,洪水含有大量泥沙,将植物中的水分吸附一空,阳光暴晒后,构成植物的元素起了变化。
塬上人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夏季的暴雨都是一片一片的,这片山坡暴雨如注,那片山坡艳阳高照,都是常事。俗话说,隔一条犁沟,都是旱涝两重天。意思是说,只有半尺宽的犁沟,这边暴雨成涝,那边亢旱成灾。这不是形容词,而是黄土山乡夏季的常态。本地暴雨,洪水中的财富与本地无关,洪水将本地的杂物搜罗出来,携带给下游了,而上游下没下过暴雨,下游人并不知道,看见河道里洪水翻卷,川里人赶往河边,都是来得及的。待塬上人看见洪水,一路奔跑到川里,几道洪峰已过,而前几道洪峰携带的杂物最多。再者,川里人早把几乎所有便于捞柴的有利位置都占据了,塬上人只能见缝插针,看着川里人的脸色,溜些许边儿。而且,都在一方天地生活,只是塬上塬下的区别,塬上人活到老,都是彻底的旱鸭子,一个村子挑不出一个勉强会水的,还普遍晕水,只要到了河边,据他们说,脚下的土地在到处乱跑,眼前的水流迷离恍惚,脚下明明踏着硬地,此时,地是软的,棉花一般虚浮,他们跟着脚下的土地跑,直接跑进水中了。在清流那里如此,在喧天洪流面前,早已魂飞魄散了。
小时候,每到县城逢集——县城在马莲河以东的高原上——马莲河西边塬上的人,下到河边,大男人在只有齐膝深的河水里哇哇哭喊,我们这些河边七八岁的小孩,牵着他们的手过河,一趟可以挣两毛钱。黄昏,赶集回来,我们再接引他们过河,一趟又可挣得两毛钱。十天一集,我们在这一天,每人都可挣得一元两元钱。在那年月,这可是一笔巨款啊,一个月一分钱不进的农户,太普遍了啊。若是早上赶集过河,中午突遇暴雨,发了洪水,黄昏时,塬上人隔在河那边,那又是一番情形。洪水要是太大,川里人也不敢轻易涉足,一般的洪水,川里的男人,半大小孩,会脱光衣服,在洪流中漂流几百米,爬上对岸,让对方,无论男女,都要脱得一丝不挂,为保险起见,还得捆住他们的双手,拉扯进洪流,在泥流中,高高低低,漂流到回水湾,拉扯上岸,让他们自己去小河沟,用清水洗去身上泥垢,川里的男性又从河岸逆流而上数百米,选一个入水位置,再去拉另一个人过河。为什么要脱得一丝不挂呢?性命相关,丝毫顾不得半分廉耻。半河水,半河泥,身上带有一丝一缕,泥水搅缠上去,那可是不轻的分量。为何又要捆住双手?不会水的人,到深水区,双脚一旦踩不到河底岩石,心中一慌,双手乱打乱抓,拍起的泥水会将双方眼睛蒙了,都被泥浪打晕了,冲走,或直接呛死,若被对方抓住,无法划水,两人的性命很难保住。
在黄土山乡,小河沟的洪水是沾不得的,河床极其狭窄,水流奔涌,夹杂着大量泥土,还有巨石,任你水性好过浪里白条,也不顶用。这与水性无关,哪怕是自己的亲老子亲儿子被洪水卷走,都是不能入水救的,白费工夫,再搭上一条命。在洪水中游泳,专指在马莲河这种大河中,水面开阔,两岸还有不算陡峻的堤岸。大河里的洪流,看起来泥浪喧天,声震远近,其实,哪怕在清水中纯粹浮不起的那种水性,只要胆大心正,你都可以一搏泥流的。因为泥流浮力大,你站在水中,双手搭在水面,都不会下沉的。你只需借着水势,遇到大浪,适时昂起头,不要让泥浪打蒙了,遇到漩涡,你将身子圈起,屁股朝下,手脚都漂浮在水面上,便不会被漩涡吸进去。我算不得有什么水性,在清水中,手脚并用,勉强浮得起来而已,而很小的时候,即可在洪流中玩水。我觉得太神奇了,多年后,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黄土高原的洪水泥沙太大,而泥沙的比重大于人体比重,所以,人体可以自然漂浮于水面。当然,我也多次遇险,淹得半死时,大人救援及时,拉扯上岸,爬在牛背上控水,缓过劲后,返身又钻进水里。河岸边所有的男孩都是这样过来的,闯过一关又一关,大人管不了,也不大管,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成长的。只是我最小的哥哥,在那一个炎热的午后,把十二岁的生命停留在门前的漩涡里。
那年我九岁,午饭后,收拾完家务,每人挎上一只草筐,手持镰刀,叫上与我同龄的堂哥,下河滩打猪草。半个月没有下雨了,热得难受,上游似乎也没有下过雨,河水平缓,门前的一段河水有一个远近闻名令人谈之色变的恶名老龙潭,约有三里长短。这里曾经淹死过许多岸边有名的弄潮儿,水域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漩涡,在平水期,那儿都会旋起一圈水桶粗细的涡流,圆圆的水圈像是一只滴溜乱转的贼眼睛,眼神如刺,令人不由心惊肉跳。岸边活着的几代有名的水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下去过。不知是谁先提议的,没有人犹豫过,我和堂哥率先入水,小哥哥接着入水了。小哥哥那时已算得上有水性了,我和堂哥只是在清水中手脚并用勉强浮得起的水平。三个人同时被淹没,原来那是一个水坑,坑口与河岸没有任何过渡,入水即入坑。我和堂哥前后挣扎出来了,小哥哥却久久不见踪影,我和堂哥慌了神,像两条被人追打的小狗,满河滩疯跑呼喊,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那天所有的大人都在半山腰一个宽阔的台地上劳动,互相间被山坡隔挡着,看不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喊叫声。还是在另一山头的牧羊人似乎看出了河滩的不对劲,他那里正好高于台地。河边发生孩子溺水的事故每年都会有多起,台地上的大人像是训练有素随时整装待发的军人,撂下工具,第一时间赶往河边。山坡漫长,连通河边的陡坡小路,走起来在四五里远近。大约半小时后,大人赶来了,几个水性好的人立即跳下漩涡,一遍遍潜水,一遍遍空手返回水面。直到太阳落山时,在漩涡底的淤泥中,捞起了小哥哥。从此,家中只剩我一个孩子了,几个大哥哥和姐姐,早已以大人的身份各自奔波自己的生活了。
村中的孩子消停了,每天都在河边溜达,打猪草,打柴,打群架,再没有人玩水了。半个月后,一切恢复常态,每隔几天都有孩子溺水,都因为救援及时,有惊而无险。直到我离家数年后,我的亲侄子,十六岁的亲侄子,第二年就要参加高考了,那个暑假在县城中学补习,回家取干粮时,徒步走过二十里山路,到河边,暑热难挨,下河凉快时遇险,我的年已花甲的嫡亲三叔正好在河边劳作,飞身下河救援,爷孙俩双双遇难。
在马莲河边生活了十六年,马莲河给了我无尽的欢乐,也给了我无尽的伤痛。我的童年少年一切的欢乐都与马莲河有关,我的童年少年一切的苦难,却不都是拜马莲河所赐。而小哥哥的遇难,对于我,实在是一桩致命的打击。虽然,在刚满两岁时,母亲的去世,已经注定了我童年和少年苦难的底色,可能是因为不懂事,倒没有觉得什么,而小哥哥是我日常生活的唯一依傍,他的离去,世界在我面前,从此一直是空茫的。这个世界与我无关,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我,假如某个物件,同时被我和另一个人看上了,那么,毫无疑问,它属于另一个人。自那之后,我没有与人争抢过什么,直到现在。金钱,名誉,地位,女人,一切引起人争抢欲望的东西。我的世界在那个夏天的午后,已完全彻底地还给了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活着,活在这里,活在那里,这样活着,那样活着,活得好坏只是别人用别人自己所认定的标尺对我的丈量,与我无关。在我觉得,怎么活着都是好的,身无分文的时候,坐拥财富的时候,迎风高歌的时候,逆水行舟的时候。凡是命运给你的,强加你的,赠与你的,你都得接受,主动的接受,被动的接受。没有什么好不好,好你也得接受,坏你也躲他不过。在他人看来,在这几十年中,我还做过不少事情,以现行的操行标准衡量,所做基本上都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将我恭维为成功人士。以这些为基点,不乏真诚地指出了我的身上的若干优点,比如善良、敬业、达观、洒脱,等等,等等,还有手不释卷,博学多识,等等,等等,让我自己看到这些词汇后,往往都要回环四顾,一时无法确定到底说的是谁。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已经确认,这个世界真的与我无关,或者,我真的与这个世界无关,所以,我才会成为这个样子,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与我有丁点关系,或者,我与这个世界有丁点关系,我的人生态度肯定不是这样子的。至少,我可以放弃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但我得郑重声明,某些东西原本是我的。
这一来,并不因为你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利益诉求,而因此获得某种安宁。相反,你因此得面临一个又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质疑:这个是你应该得到的,那个也是你应该得到的,你为什么要放弃?遇到这种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鸣不平的人,我除了内心感动,还有内心的悲哀。我只有虚言应付,或傻笑搪塞。当然,有时我也会较真,我会反问:什么是你的,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你的?你出世时,你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你离开世界时,你打算带走什么,你又能带走什么?你见过谁出世时手里带了东西,你又见过谁是带着东西离世的?什么是应该?应该的事情很多,数不胜数,你应该这样,同样也应该那样,人活在世上,真的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你,我,他,所有人。成功人士往往会给人讲自己的励志故事,渴望成功的人也手捧这种励志故事心潮澎湃,那么,你不妨照猫画虎试试呀。他的成功之路只是他的,只是他已经走过的那条路,那条路当他走过后,已经化为一条概念中的路,一条画布中的路,定格的路,定型的路,永恒的路,永久废弃的路。别说对于你已经此路不通,不信试试,让那位成功走过这条路的成功人士再踏着自己走过的脚步重走一遍,说不定会走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更成功,也许一塌糊涂,但绝非原来的样子。
版权声明
为加强原创内容保护,日前,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各子报、甘肃新媒体集团各平台已将其所有的版权统一授予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维权及给第三方的授权许可。即日起,上述媒体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刊登的,包括文字、图片、摄影、视频、音频等原创作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以及H5、海报、AR、VR、手绘、沙画、图解等新媒体产品,任何机构、媒体及自媒体未经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许可,不得转载、修改、摘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并传播上述作品。
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致电0931-8159799。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
相关新闻
- 2020年09月27日会宁将举办红军会师地区地标产品特色产品展示交流活动
- 2020年09月27日礼县:直播带货开辟苹果销售新路径
- 2020年09月27日[专题]清水县脱贫攻坚主题成就线上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