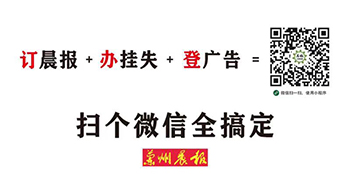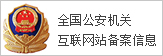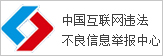为民族精神元气护法问道
——《敦煌本纪》的历史理性与诗意情怀
阎小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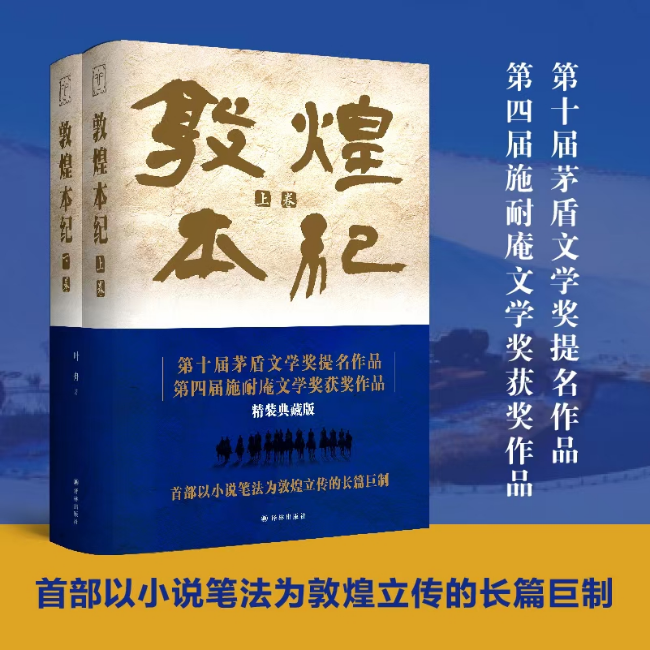
敦煌,是世界艺术长廊,人类文明宝藏。敦煌文化,是古代中华文化的缩影,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象征。“敦煌学”被称为“国际显学”,是当今“大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敦煌”的纯文学书写向来寥寥。《敦煌本纪》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敦煌母题最宏大、最深广、最精微的文本呈现。《敦煌本纪》以敦煌众生为主体,直追民族精神根脉,书写了历史风云、世道人心和时代尘埃蒙蔽已久的“春秋大义”,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敦煌本纪》作为一部史诗型巨制,是一部敦煌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和精神生活史,也是一部边地家族史,因其孜孜于揭示敦煌文化精神和历史传承的本来面目,因此具有“正史”和“信史”的品格与认识价值。《敦煌本纪》充满对理想人格的吁求,对家国情怀的张扬,对人道立场和人文关怀的执念,终归取决于叶舟深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完成对敦煌文化之正法真义的诠释。同时,叶舟把敦煌这一博大而抽象的文化资源有机化为小说的内在资源,将敦煌文化灌注于作品的肌体当中,以高超的感知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再现了一个生动的敦煌风物图和河西走廊传奇史,小说文本充满文化意蕴即“敦煌味”,这个庞大而新鲜的艺术世界,是叶舟对敦煌最好的致敬和供养。

《敦煌本纪》叶舟著 译林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一、 春秋大义与民族元气
《敦煌本纪》首先是一本书写春秋大义的书。《敦煌本纪》通篇围绕“义”在来展开。作品开篇即讲:“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刚勇英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①如此冷峻凛冽的开头,凿开了时间之冰河,启动了历史之暗门,大义之书由此开篇。
敦煌故事由索门“义庄”起。义庄既是敦煌人心中的圣地与息壤,更是敦煌大地数代子民的精神乌托邦,义庄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容置疑,官署兵营、长老乡贤、兵匪盗寇、僧俗朝野,无不对义庄高山仰止、顶礼膜拜,皆因索氏七颗脑袋、六代爷孙传承下来的一件血衣,凝结着仁义、侠义、道义之高德威仪,也是我们民族传统道德骨血中的血魄精魂。“有索门在,这敦煌就有了主心骨”②,索氏一门为何如此荣耀?并非传人索敞之个人德行,乃敦煌人崇德尚义的自觉。养尊处优的索敞,承袭索门的血衣,却朝兢夕惕、如履薄冰,他既因索氏一族传承血衣的庄严与荣耀而引以为豪、风光无比,又惶惶于出人头地、扛旗举义的重大使命旁落或难以为继,但索敞的德行、格局、心胸和能力,实际上已经无法承担义人之首领。索门不幸,家道中落,索敞遭遇厄运,敦煌大地上世道人心的乱局开始了。尽管索氏之后人索朗沦为丐类,但义庄之精神地位并没有就此立刻消失;尽管围绕名利得失,河西走廊上乱象丛生、纲常紊乱,但没有新的力量能够真正代替义庄。阴鸷狠毒的丁荣猫虽然机关算尽,毁掉义庄,毁掉索门传人索朗,攫取了敦煌城实际控制权,但它最终不敢公然更换义庄招牌,这就是精神威力,是敦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他人、周围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春秋大义其实是“历史大义”。中国传统认为,历史中是存在大义的,而大义也必须因历史而存在。没有无大义的历史,无大义的历史也是无意义的。同时,大义也不可空存、独存,而必须由历史时间所承载。
义,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中庸》载“义者,宜也”。孔子看来,在社会生活中能自觉按照“仁”的精神和“礼”的原则做出合理的判断并能在行为中实现的品德即是“义”,即行为上的合宜和应该。《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把“仁义”作为道德规范通过调解家庭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实现其“王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实现自身价值和培养自身道德修养,生出“浩然之气”,培养正义感,进而成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精神力量。
神圣的义庄倒了,义人并未绝,胡家后人胡梵义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敦煌大义的举旗者。梵义接上这面旗帜,正是群龙无首,世风沦丧的乱世年华。懵懂少年因父亲的突然患病,不得已匆忙间担起了复兴家族的重任。他默记并兑现父亲的承诺,用十余年光景为索门开了一座义窟。他为父求医,走上陌路险途,历经九死一生,却结识了洪门领袖,团结了飞行游击、拯救了孔执臣,襄助孔祥鹤施救疫民。他团结组织沙州城内的热血青年,歃血盟誓,成立急递社,河西走廊的交通动脉和物流贸易通道由此畅通安全,成为敦煌西出东进的信息网和保障线。敦煌藏经洞的文物面世后,他果断出手、力挽狂澜,与孔执臣合作,截留并仿制了成千上万的文书、佛经和卷子,狸猫换太子,保住了这批千年珍宝。丁荣猫构陷索氏得逞,控制敦煌,推行鸦片种植,梵义领导的急递社不顾威逼利诱,毫不妥协,继续扼住了这一片边陲之地的大路小径,不曾输出过任何一枝邪恶之花;也正是因为梵义的大义凛然,得罪了与丁荣猫狼狈为奸的酒泉洪门,当年的结义兄弟背信弃义,联合酒泉驻防团,合力绞杀急递社义士,急递社溃散。更痛心的是,与梵义世交两代、贤能良善的开元寺住持拖音与梵义长相酷似,遭洪门误杀,替梵义而死。拖音一死,莫高窟无人掌管,梵义毅然割断尘缘,顶替拖音隐姓埋名,成了莫高窟沉默的守护者……
梵义作为《敦煌本纪》最重要的人物,自始至终以其行为践行一种大义之德,这是全书最重要最鲜明的思想指向和精神标杆。梵义作为一名动荡时代边陲乡土少年,始终秉持父亲的教诲,坚持做一个“精良的人、纯明的人”,奉行高义大爱,九死而其尤未悔。梵义身上的义,不是飞行游记的快意恩仇,不是独来独往、虚蹈古风的名士清流;也不是自命清高、坐而论道、附庸风雅的隐士高人,他以牺牲为己任,以担当为天职,灵魂伏地,肉身隐忍,躬行河西大地,甘愿在人生的大光阴中“生做马,死做车,一辈子走下去”③,他是正义和真理的不倦追随者,是苦难和邪恶的克星。以梵义为主线,敦煌大地有一大批义士前赴后继至死不悔。率性阳光、忠诚坚韧的梵同,自尊要强、果敢激烈的梵海,心念苍生、舍身救民的孔祥鹤,忍辱负重、乐善好施的沈破奴,清高自持、隐忍勤勉的孔执臣,高风峻节、护法殉道的印光、拖音,淡泊清平、睿智刚正的丰鼎文,侠骨豪气、勇毅血性的陈小喊……一个个个性迥异,血肉丰满的义人,在乱世敦煌这片道德、秩序的废墟上,或抱团结义、并肩生死,或殊途同归、彼此默契,泅渡茫茫苦难,对抗邪恶阴谋,艰难地迎取着救赎、修复和新生。
义,在中国生生不息传承千载,一方面义常被排斥在传统法律和礼仪之外,另一方面义又作为潜在的“礼”而存在。义的精神在战国时期特殊的环境中就大放异彩,其时主要体现在侠义之士身上,并以沛然不可抗拒之势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战国策》浓墨重彩记载众多侠义之士,《韩非子•五蠹》将侠儒并论。战国精神感动了司马迁,他在《史记》中专设《游侠列传》,《史记》在精辟凝练战国侠义精神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侠义精神的敬佩与渴望;班固对战国侠义精神的诠释,不仅承认游侠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与特殊价值,而且还肯定了战国侠义精神“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品质更之难能可贵。自汉以降,儒学渐盛,正史少载游侠,但魏晋以来,侠的文学作品蓬勃生长,侠的形象在诗歌、小说、杂史中大放异彩,侠义精神传承不息。
鲁迅终生致力于挞伐“国民劣根性”,呼唤和寻求“人的现代性”,对民族精神中的“义”,同样充满吁求和礼赞。他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认为,这些正史所不屑的人,正是中国的脊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际,一本《故事新编》,幽暗奇崛的笔端,仍充溢着对大义的景仰,对不义者和假仁假义者极尽嘲讽。《铸剑》表达对生命、牺牲和情义的独特理解,《奔月》写落寞英雄的困窘,《非攻》写墨子以一己之力拯救一国生民,表达了博大的人间情怀,一种深厚的人道精神;《理水》《出关》《采薇》通过小我与大我、隐与显、退与进、坚持与妥协,都可归结为对义的思考。
书写大义,呼唤大义,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的自觉选择。“仁义白鹿村”的白嘉轩,浸润着秦汉文化的血脉,以及那块土地的山水风云和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精神;朱先生更是心载“天地良心”四字,只身却敌、勇禁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为了胸中大义,最后绝仕进、弃功名、著书立说,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气节。《古船》中作为资本家后代的隋家子弟尽管建国后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但在道德人格上表现出一种大义之风,抱朴对待洼镇狸灾祸与苦难的人道情怀,含章作为一介弱女子为哥哥做出的牺牲,茴子为保全家族与自身贞洁与隋家祖屋共存亡之举都昭示出主人公人格上的坚韧与决绝。《红高粱》中的于占鳌,狂放、不羁的独特个性和不屈不挠的抗争义举让我们震撼,展现出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英雄主义的豪气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些一以贯之的经典形象,在绵延传递着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历久弥新的春秋大义。张承志始终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倡扬“清洁的精神”,崇尚“奏雅乐而行刺”的武道,“咳热血而著述”的文途,把“不顾生存求完美”的历史大义推向极致。
精神性是文学的核心特征和灵魂,任何缺乏精神启迪的文学,不论他表现得如何精致,终究会被读者和历史抛弃,文学的精神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和对它的接受水平。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无比丰厚的,优秀的作品总能化解整合这一资源,并将其化为丰富的信仰,化为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但大量作品放浪于形式的逐新,津津乐道于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把生活仅仅还原为“过日子”,或沉迷于暴力、娱乐、血腥和戏谑,缺少人文关怀和精神关怀,不屑于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让小说疏离读者放弃教化,丧失了应有的使命担当。以叶舟的才情和写作经历,对时尚表达和对事物的解构能力,完全能够创造出喜闻乐见、轻松刺激的畅销篇什;以叶舟对敦煌的知识积淀和情感储备,完全可以完成对敦煌历史的传奇戏说和演绎推介。然而,他却以二十年韶光为敦煌赤子苍生立“本纪”,直追民族精神的根脉,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敦煌本纪》构建了一座二十世纪初的敦煌沙州城,并且要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一群群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进而“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④这份元气,就是被历史风云、世道人心和时代尘埃蒙蔽已久的“春秋大义”。
叶舟笔下的“义”,不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僵化继承,不是主观意志的强力说教,而是从近代以降敦煌大地历史风云变化和敦煌子民生存搏击与命运抗争的真实生活中自然流淌的,是叶舟静听佛陀神示、迫近敦煌心脏、感知众生魂魄之后的幡然顿悟。敦煌之“义”,传到义庄索敞这一代,索氏一族也好,胡氏、沈氏也好。对这份传承有一种惶恐不安的焦虑,他们不知道如何继承这份遗产,不知道如何安放这件耀眼的血衣,不知道如何擦亮这面旗帜,心怀敬佩又重负异常,围绕开凿“义窟”这一承诺,在老一代义人心中从此打下了一个巨大的结,这个结在他们一代人始终没能打开,而是愈加沉重,直至把他们压垮。究其原因,就是这个“义”在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写法,当义作为一种殊荣,一种标识,一种昭彰一己私利的旗帜,义庄之种种“不义”与不堪,就预示着这个作为传统道德象征的“义”已经走向死亡。何去何从?新一代义人来了。“精良、纯明”的少年一代胡梵义们让义复活并获得新生、升华。胡梵义开创的这种大义,包含热血、狭义、极致,充满救赎、牺牲、担当,特别是通篇激荡着一种激昂的青春气息,那就是叶舟概括的少年中国之气,这种气质和气象,使得敦煌新一代义人梵义们不仅成为一群有个性、尚勇武、讲信用的群体,更是重担当、懂感恩、讲公正、顾大局,既有感天动地的悲悯之情,又有冲塞天地的斗争精神,这种少年气象、青春气质,为敦煌之春秋大义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也为中国当代小说提供了独特的性格典型和新颖的审美经验。
版权声明
为加强原创内容保护,日前,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各子报、甘肃新媒体集团各平台已将其所有的版权统一授予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维权及给第三方的授权许可。即日起,上述媒体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刊登的,包括文字、图片、摄影、视频、音频等原创作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以及H5、海报、AR、VR、手绘、沙画、图解等新媒体产品,任何机构、媒体及自媒体未经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许可,不得转载、修改、摘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并传播上述作品。
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致电0931-8159799。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
相关新闻
- 2021年05月23日用严谨虔诚的文字开凿敦煌文学之窟——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精装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分享会侧记
- 2021年05月23日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作品分享会在敦煌举行
- 2021年05月23日用严谨虔诚的文字开凿敦煌文学之窟——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精装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分享会侧记
- 2021年05月22日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作品分享会在敦煌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