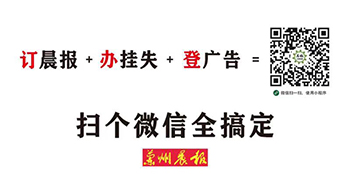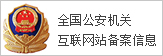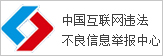上海书展期间,叶舟签售《敦煌本纪》
二、历史与心史
《敦煌本纪》是一部敦煌秘史,更是一部敦煌人心史。叶舟说:“这部小说试图去重新发现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得今天的力量与担当”⑤,生于大西北的叶舟,向来以这片苍凉古旧的大地为自身文学版图,而敦煌在他眼里则是一枚黄金的钉子,钉住了他的文学版图。从少年时起,敦煌就对他形成了最初的震撼,继而使其对敦煌保持了长久的皈依。叶舟以敦煌为母题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随笔,构建了他创作生涯中庞大的“文学敦煌”世界。但面对这座文化宝藏、精神富矿和艺术殿堂,叶舟越发觉得,“一定要写出一个大部头,一步心血之作,道出敦煌的秘密,说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让那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去占据舞台的中心,并以此作为我这个儿子娃娃的反哺和报恩”⑥。一经发此宏愿,叶舟便以全部热情和精力沉入河西故道,进行了长久的体验、感知、储备和构想。
张承志曾说“历史过程影响着人的心灵,现在人们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兴趣或许多于对自己政治经济历程的关心。所以,心史——人类历史中成为精神文化的底层基础的感情、情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应当是更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⑦他认为“在高深的历史学面前总有点谦卑的文学,在比较和挖掘中又被揭示一层意义。对历史的文学式发想并不是总该挨人轻视”⑧,因为“历史长河淹没了那么多人心的活动”“历史本身也应当是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历史”⑨。敦煌是历史的、人文的、艺术的敦煌,任何科学诠释和虚无演绎都无法真正富含深沉博大、多元复杂的敦煌魅力,“但敦煌,终究是人创造的,敦煌精神终究是人维系,天地人佛之间人终究是主体,在人世之间,生民才是主流,在历史转型时期,礼失求诸野,到民间寻觅敦煌精神的真谛”⑩,《敦煌本纪》截取的恰是被时代忽略,正史所阙如的上世纪初三十年,叶舟没有流连和拘泥于历史的学术面貌、纸上概念和具体形态,倾其豪情、才华与大爱,与深爱与景仰的敦煌苍生、田夫故老一起呼吸,一起悲喜,一起感受人世上盛大的光阴,迎接生命中不绝如缕的困难,终于找到了敦煌在世界的活态延续,写出了敦煌人的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揭示了敦煌文化精神和历史传承的本来面目。
《敦煌本纪》是一部边地家族史。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犹如国家的基础,故有“家国一体”之说,家族世系书写,也是现当代小说常用的表现形式。因为家族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优秀的家族书写往往是优秀的民族史书写,因为它是“通过一个初期的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敦煌本纪》的故事是以敦煌城三姓家族的兴衰沉浮为主线,但极具地域文化和历史面貌的独特性。中国传统家族形态最大的特征是宗法制度、礼俗文化和血缘伦理的强大根性影响力,如果说《白鹿原》写的是作为王朝旧都、农耕文明渊源地的关中平原的传统家族世系,叶舟写的家族史,则是上世纪初,清廷欲坠、时局动荡,河西走廊边地一隅,这是一段锈迹斑斑的时代弃儿,是一块独特的移民群落,是一块孤悬关外的精神“飞地”,这与我们所熟悉、艺术作品屡屡呈现的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家族历史是有区别的。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向来举足轻重。汉唐以来,一直为关西军事重镇。西汉时初置郡县,以敦煌名之。此后千余年间,敦煌建制屡有废置,归属名称亦多有变更。明初于敦煌置沙州卫,正统以后,国势渐衰,敦煌等地渐次丧失。嘉靖初,尽徙关西汉民,退守嘉峪关,此后至清初近两百年间,敦煌旷无建制,遂成蛮荒之地。清康熙后期,嘉峪关外渐次恢复,雍正元年置沙州所,三年升为卫,又置安西诸卫,成清朝势力继续西进的基地与桥头堡,大批将士从内地西迁,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开始大量迁徙内地居民。雍正四年,开始从甘肃各州府往敦煌迁入大量移民。移民到敦煌后,又按各自迁入地划区设隅建立“坊”统一归置管理,垦荒屯田,重建敦煌。其时,敦煌已废弃近两百年,境内人烟稀少,不成村落,几成化外之地。官员派往敦煌,也被视为畏途荒路,时人描写敦煌为“风摇棰栁空千里,日照流沙别一天……清时代宇重开辟,感旧犹恋蔓草烟。”(11)
清末民初的敦煌,正是这种独特的“农坊”制度发展完备后重新走向衰落的边地移民群落,这一群人来自内地,既是甘肃本地的原住民,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者,负载着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的烙印,同时经过数代人的迁徙流寓、杂合聚居,文化心理、民俗风情、生产生活习惯都有许多独特之处,他们是大地的主人,但总隐约有一种漂泊游离的动荡感。《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屡屡信誓旦旦地教育后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底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而胡恩可教导儿子梵义时却不无忧心地说“我们没别的命,我们的命就在河西一带,在敦煌一线。我们也没有另外的大光阴,我们的光阴,就是活在这条长路上,生做马,死当车,一辈子走下去”(12)。在敦煌,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法制度、民间乡贤治理共同构成敦煌地方文化,江湖帮会、商旅游击、异邦人士,尽在敦煌大地悉数登场。索敞、胡恩可、沈破奴、李豆灯,虽在二十三坊间共存共处,但每个人的身世、背景、性格都背负着一些隐晦而神秘的禁忌。义庄掌门索敞虽家底殷实,优裕富足,表面上备受尊崇,但他一出场就显得忧心忡忡、患得患失,出门唯恐折了义人尊严,睡觉都盘算着出人头地、遏制对手,维护索氏的永世英明和龙头地位。胡恩可貌似深明大义、公允慷慨、八面玲珑,谋划为索家捐建义窟,为沈家新修宅院,原来却是打着他精明的人生算盘,全是为了为子女攒足名声,铺平道路,奠定福禄绵延的康庄大道;沈破奴虽与世无争、谨小慎微、克己向善,严守精神纪律,但他又深藏自身身世,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时时流露出逃离和退缩的悲观情绪,始终没有直面人生,没有突破自我。这些人物身上,处处飘忽着一种不安和焦虑,这种性格,是区别于农耕文明大背景下宗法社会超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和道德惯性,他们身上有着早期商业资本家的投机本性和原罪意识,不能否认他们身上存在的进步性的因素,但这些进步的萌芽时时被厚重的道德焦虑打回原形,体制力量的衰微、民间自治机制的失效,让敦煌在东西交汇、新旧角力的夹缝中,在生存竞争的飞沙走石中,宗法文化余晖将尽,在佛陀无声的垂怜和护佑下,希望只能指向“纯明、精良”的新生一代。

《敦煌本纪》是一部凝结着宝贵历史经验的“信史”。对于《敦煌本纪》的史传价值和史诗品格,已有多人论及。但《敦煌本纪》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型作品。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型作品常指历史背景庞大、地理环境广阔、人物形象众多、主题内涵丰富,且必然涉及重大社会历史叙述背景。《敦煌本纪》讲述三大家族的兴衰,上百号人物的命运,三十年人事动荡变迁,一百余万字的体量,构建起一个及其壮阔复杂、浩繁缜密,囊括天地人佛,深含人间烟火的立体的文学世界,但支撑这一庞大艺术世界的,并不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经典史学理念、人物,换言之,这些人物不是从历史本位出发进而求全、印证,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叶舟是从敦煌芸芸众生出发,从艺术形象和美学感知出发,再造了一个丰盈而鲜活的敦煌世界和敦煌人物谱系。这是极具艺术冒险精神和创新勇气的大胆之举,也保证其作品艺术生命力、独创性和认识价值。一方面,叶舟力辟所谓的传统宏大叙事,甚至刻意提防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和主流价值的注入,他不是按照“应有的”历史面目去按图索骥,而是一切从艺术本体和人物性格、命运的自在规律出发,一任人物宿命在自身道路上冲撞搏击。例如,“普天共和”的消息传到敦煌,梵义不自觉卷入了所谓革命的狂欢,但梵义“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这改朝换代的一天所降赐的礼物,慌忙扔掉了传单,埋下了身子,生怕别的少年讥笑”(13)一描写极具意味,或许可以窥见作者对社会历史题材创作的态度,他不愿意落入复述历史经验,为印证所谓众人皆知的概念曲意制造人物,虚构所谓高大完美先知先觉的英雄形象,这是叶舟呵护人物形象的纯粹性,从真实的人性和时代语境出发,遵从人物命运发展的真实路径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这一态度也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和地域实际的。革命的启蒙,在彼时的敦煌,只是虚无缥缈、片言只语,梵义不是也无法成为时代的进步人士,他是在严酷动荡的生存竞争和灵肉搏击中隐忍前行所谓的平民英雄。同样,对索乘的描写,作者也丝毫没有拔高,冷酷、道貌岸然、满嘴新词又唯利是图,醉心于强权、杀戮和攫取,暴露了早期革命党人队伍中投机者的真实面目,加深了敦煌历史的悲剧意味。对于梵同出走敦煌奔赴延安,也只是侧面描写,轻轻带过,为敦煌少年中青春、智慧、勇毅的力量安排了一条真正有希望的出路,大义敦煌终有归宿。总之,《敦煌本纪》始终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掘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同时叶舟仍然始终坚持清醒的历史理性,只是以极富魅力的个体文化价值的发掘,还原了时代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了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因此,《敦煌本纪》应该不同于以往的“史诗”型长篇,但可看作是一部凝结着宝贵历史经验的“信史”。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叶舟和《敦煌本纪》
版权声明
为加强原创内容保护,日前,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各子报、甘肃新媒体集团各平台已将其所有的版权统一授予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维权及给第三方的授权许可。即日起,上述媒体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刊登的,包括文字、图片、摄影、视频、音频等原创作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以及H5、海报、AR、VR、手绘、沙画、图解等新媒体产品,任何机构、媒体及自媒体未经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许可,不得转载、修改、摘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并传播上述作品。
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致电0931-8159799。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
相关新闻
- 2021年05月23日用严谨虔诚的文字开凿敦煌文学之窟——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精装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分享会侧记
- 2021年05月23日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作品分享会在敦煌举行
- 2021年05月23日用严谨虔诚的文字开凿敦煌文学之窟——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精装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分享会侧记
- 2021年05月22日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作品分享会在敦煌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