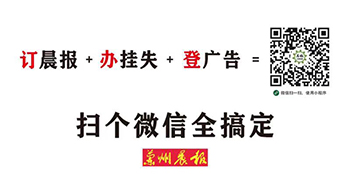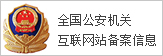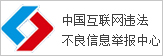2014年,李书喜代表《读者欣赏》杂志采访了陈天铀先生,重点谈西部山水画创作,此访谈连载于2015年《读者欣赏》杂志(1—12期)之“名家风采”栏目。
一
李书喜:从小历经的磨难养成了您坚韧的性格,您的画里面也充满了这种力量和张力。那么,您艺术风格的形成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它们之间是如何互为表里的?
陈天铀:当然有一定关系。我比较喜欢画山水,实际上有一个情结。1958年,我刚上初中,正是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当时炼钢需要白云石,学校就组织学生们到天祝乌鞘岭后面的白云石矿去劳动。我们10月份进山,到来年元月份出来,差不多干了3个月。
冬天的祁连山很冷。我们从山上把石头挖出来,用背篓背下山,再用架子车把石头拉到火车站。虽然天天重复这样的劳动,但也觉得这种与自然的亲近很有意思。当时,兰新铁路刚通车,刚好此时石鲁先生画了一张《火车来了》,这幅画就是在乌鞘岭画的。
当时的乌鞘岭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出永登以后,几乎是没有人的,天祝一带不像现在有住户,当时全是草滩。而且进了草滩以后,因为草比人高,人是看不见的。走了好几里可能会碰见一个帐篷,有几个人在放牛牧羊,之后又走进不见人烟的草滩。劳动结束后,凝视苍茫神奇的马牙雪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心灵,祁连山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神山。自此,我爱上了河西走廊,爱上了祁连山,爱上了大自然。可以说,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二
李书喜:画作贵在精神,画的精神需要具体的笔墨来表达,您是如何认识笔墨并形成自己的风格的?
陈天铀:我对笔墨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幼年时期,我遇到一位姓陶的老师——北京名家王梦白的学生。他有很多画册,那种影印的珂罗版的画册,他还教我怎么画。1956年,我家和张大千的二儿子张心智住邻居。张心智的夫人看我在院子里画画,感到很稀罕,时间长了以后,就叫我到她家,看张大千的一些画册。再加上张心智的指点,我对笔法有了初步的认识,明白了中锋、侧锋的用笔,懂得了墨分五色,开始认识到笔墨的重要性。
后来,胡佩衡先生的学生赵翀先生由铁道部文工团至兰州铁路局,他是我父亲的旧交,毕业于辅仁大学,是抗战前北京湖社的画家,是他引导我窥见中国笔墨的奥秘。他认为明“四家”之一的沈周笔法雄浑厚重,由沈周可上溯北宋的范宽、李成。从沈周的画入手,可避免清“四王”画中的一些习气。因此赵翀老师找了很多沈周的画册,叫我临摹、学习。慢慢地,我认识到用笔的“拙”“厚”“苍劲”,以及笔墨的气韵、气象、意趣。后来看了黄宾虹先生的画论以后,明白了五笔七墨,对“平、留、圆、重、变”五字诀有了深刻的理解。从那时起,不管写字、画画,都注意用笔的变化,让“平、留、圆、重、变”的运笔方法成为一种自觉。
1963年春节,西安钟楼展出的迎春画展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展览。这个展由石鲁主持,汇聚了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李梓盛、康师尧等大家。在参观展览中,我发现赵望云、石鲁等大家画的是青海祁连县到甘肃民乐扁都口这一带的风光,有藏民、雪山、杉树、草原、戈壁。他们用中国传统笔墨描绘大西北真实的山川,表现得那么真实可信、生动自然,让我由衷地钦佩而且下定决心以他们为榜样,画出陇上的山川大地。后来,我去西安见过一次何海霞。老先生给我讲了些最基本的东西,如何用笔、怎样写生。我感觉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探索大西北山水画笔墨语言的钥匙。
甘肃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尤其是河西走廊的自然景观,与陇东截然不同。整个大西北,包括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及内蒙古西部,基本上由雪山、草原、戈壁、沙漠、风蚀丘陵构成,这里自然景观荒寒浑厚,地貌特征奇异神秘。传统的中国山水画里面找不到表现这些东西的语言,这就需要在写生的时候边观察边思考,在传统中国画笔墨基因中找到与景物相关的契合点。我认为这种探索要面向传统,研究传统山水画家在运用笔墨之时与表现物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找到这些特点的精神内涵。
大约在1979年,甘肃美协接待关山月和黎雄才到甘肃来讲学、写生,黎先生强调写生必须画得真实具体。对山岩结构、山脉之走向、树石的关联、水流的趋势等均应交代清楚,否则时间一长便分不清东南西北,极易形成概念化而缺乏具体鲜活的形象。这是黎雄才的观念,岭南画派强调这么做,可何海霞先生反对这样的写生。何海霞曾跟张大千一起在青城山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不能看完以后马上画,不能照着现场去画,而是有一个思维沉淀的过程,要让真心打动他的景物浓缩成有特点的笔墨语言。所以何海霞认为写生的时候,现场画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目识心记,读懂面对的景物。当然,在看的时候,就要思考历史的沉淀、内在的结构、形象的文化内涵、形象语言的审美特征等问题。只要具体的山川景物在大脑里沉淀下来了,最精彩的东西也就留下来了。石鲁、何海霞的好多画都是这样完成的,他们能够抓住最精华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中国画应该提倡的。
实际上,李可染先生的对景写生、黎雄才先生的写生必须画得真实具体和何海霞先生倡导让时间过滤一下等观点,我觉得这和中国画的精神观念与技法认识有关,即如何辩证认识中国文化中道与器、艺与技的问题。也就是说,技术的东西比较容易掌握,但艺术思想更重要。所以更应该注意艺术思想和艺术观念。对西部的画家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万物生机、宇宙苍茫、人生万象,从画面的有限到联想的无限,从瞬间到永恒,微妙微茫、相反相成,在似与不似中表达心像。
三
李书喜:在您以前的画作当中,生命的迹象较少,有人物的更少,从画册和市面上很少见到,而这两年在您的新作中却出现了很多的高人隐士,是不是您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陈天铀:不是这样的。山水画不管是否画了人或动物,都是人生命的体现。画家从生命的角度思考,艺术是终极真实的沉思和探寻。我这几年致力于艺术精神和笔墨锤炼,试图在生活的积累中完成笔墨语言的转化,这就需要向传统学习。于是,我近年在意临、背临中画了不少更接近传统山水画的小画,其间也表现了古人隐逸休闲的情景。
李书喜:以前您的山水画作里面鹿和大雁的点景相对多,这两年人物点景画得多了,尤其是古代人物。
陈天铀:是的。人物点景最早的时候也画过一些,这些年,我又觉得这些内容有情趣。表面上是个隐居的题材,实际上是自我修炼的过程,我这些年读了好多的古画,通过这种读画方式找到感觉再分析它的笔墨结构,然后再画。从美术史研究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深入分析研究传统笔墨技法的同时,了解古代文人山水画的创作思想。我在反复读古画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把它的隐逸思想带过来了,顺便就画个茅屋,或者临流观瀑、草堂读书、巡山访友等。这也是对现代写生的一种补充吧。
李书喜:在您有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以后再拿传统来补充自己?
陈天铀:不断地从传统去求教,我能得到一种支持,时时刻刻从传统中寻找中华文化精神的支撑,西方的东西可以吸纳接受,但是中国本土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继承、要发扬光大。
李书喜:也可以理解为您在反复学习传统的过程中顺其自然形成的一种结果?
陈天铀:是的。
李书喜:现在很多大家虽然艺术风格不同,但是艺术主张和追求是有类似之处的。您前面说过艺术体系,似乎您和贾又福、王文芳属于一个大的探索体系,但是又都有各自的发展,他们的存在是否让您少了一些孤独,并得到一些启发而令您喜悦?同时也因他们抢说了一些您想表达的艺术语言而令您烦恼?
陈天铀:贾又福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山水画领域最有成就的大家之一,他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他更是一个呕心沥血的理论思考者。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中,以儒家为骨,道释为用,使天地精神与时代思潮对接,用画笔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同他的交往中,我看到了自己艺术追求的方向,坚定了我立足西北、创造新时代西北心像的决心和信心。王文芳先生也是我最喜爱和钦佩的山水大家。他以丝绸之路为母题的山水画有强烈的形式感、厚重的体积感、悠久的历史感和崇高的境界感。他真精内蕴、大美不言的审美意识和鲜明的个性影响了一批甘肃的山水画家。1985年,他从定西办完学习班后来到兰州,在省美协办了一个小型的内部观摩展,我去和他聊了好几个晚上,对我有很深的启发。我认识到“身行万里半边天,归来还看自家山”,坚定了我以河西为基地、以祁连山为母题的山水画创作决心。
四
李书喜:您的画作主要以甘肃为主题,您的艺术探索之路和贾又福、王文芳属于一个大的体系。这也许使您少了点孤单,但同时他们又“先占”了一些艺术表达的语言,有没有这种烦恼?
陈天铀:最初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探索,基本上就是我现在好多风格的雏形。1985年前后,大家都在探索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语言、方法、图式。像贾又福先生,开始也是有人否定有人追随。实际上我和王文芳先生是互相影响的,王先生曾开玩笑说,我们成了师兄弟了。他的导师是秦仲文先生,刚好我的老师赵翀和秦仲文的关系很好,他们当时都跟过胡佩衡先生。有一段时间,我和王文芳先生谈得比较深,后来通过他认识了贾又福先生。贾又福先生有个特点是认定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十分坚持,这种坚持不是常人能比的。他开始做这种探索的时候也是一片反对之声,但是他一直坚持,直到成功。这种自信、定力和毅力让我由衷地钦佩。从这点来讲,我比较惭愧,我在探索的时候,有时候如果画的东西别人反对,我就退回来了,不够坚定,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干扰。说老实话,这是自信心不足、学养不够,也是浅薄的表现。
李书喜:我倒认为,贾又福、王文芳两位先生和您,不说艺术高低、影响大小,其实各自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的。他们各有各的一条路,您当时可能为了避开他们,选择走自己的路,做出了修正。您这条路的形成是否和他们二位有相伴而行却以求不同有关系?
陈天铀:区别还是要有的,我在进甘肃画院之前曾一度画得特别黑。在画院里我开始研究很多北派的东西,对斧劈皴,对大斧劈、小斧劈,特别是折带皴加以研究。甘肃这边裸露的山石确实是这样一种结构,所以这些技法确实用的比较多,比较上手。这和贾又福先生画的太行山有相同、相似之处,太行山也是那种岩石结构的,那种大块的岩石结构他依然要用斧劈皴,要用钉头鼠尾皴来表现岩石的坚硬感和厚实感。一样的取法画着画着就容易撞到一起,人们会觉得你这种东西怎么那么像贾又福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再找找西北的特点。青藏高原都是很大的山,但是你到跟前去看,它并不是很雄伟,它没有泰山、华山和太行山的那种高耸、雄伟。果洛州的玛多、久治县的山都就是些小山包,那都是很有名的山。格尔木、昆仑山口,一堆土山包包,虽然海拔极高,但每座山与地表的垂直落差并不大。我们想象当中的昆仑山怎么是这样的?这就是另外一种理解。反过来看祁连山,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各个时期去看,千变万化,有好多种不同的样式。从吐鲁沟这边进去,沿着互助北山一直往门源走,看到的是一种祁连山风貌;到了张掖,进到祁连山里头,又不一样;转到青海,从祁连县进去,它又是不一样的;直到祁连山最西面的党金山,就在敦煌西南面,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相对面了,那更是完全不同。我觉得反倒是这些山岩地貌能够代表我们甘肃的一些很有特点的东西,所以后面我就从这些地方入手,祁连山的柔美和粗犷得到全面表现。刚好和贾又福、王文芳拉开了距离。1995年,甘肃画院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展览,其间我曾到中央美院拜访贾又福先生。有些人认为他的画中蕴含的老庄、禅宗的东西多,实际上还是儒家的精神多,真正是恢宏刚正、光明正大的气象,有一种浩然正气。要抓住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我得到的启示是:钻研理论,对文化进行不断地思考,从大文化的高度、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艺术,再到具体的绘画。以儒家为本体、以道释为用,使天地精神和时代思潮对接,从景象到心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做到“大美无言”。
五
李书喜:您对老子非常喜欢,也有研究,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搞学问吸收的越来越多,它是一种积累,没有个性,没有自我。为道,是说为艺术,它需要有自我、有个性,而且表现为完全的自我。您在为学、为道之间有什么矛盾,在您身上有什么具体的体现?您是怎么解决的?
陈天铀:画画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的确是这个样子,你在积累和吸收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充实自己,到一定程度以后共性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大家的区别就很小了,那么个性的东西怎么体现?每个人个性的东西都像一种命运的安排,默默地影响着你的一生,一个是你先天的才情,一个是后天的阅历共同形成的,不可能两个人完全一样。我学写字有这样一个体会,小时候,家里要求学一些正大气象的东西,写颜体,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在写颜体,但写的并不一样,虽然大家在用笔、结体、章法等方面刻意地追求像,但是每人就是不一样。它不可能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画也是这样的,都是一个老师带的学生,最后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共性中间去找个性,在强调个性的时候又不脱离共性。共同的审美要求从全人类来讲,它是有共同的审美价值和趋势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强调个性、地方性的时候,还真不能忘掉共性,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偏颇的。
李书喜:您的两种思想活动是怎么转变的?孔孟、老庄、禅,需虔诚地去读,否则体会不到,吸收不了,但在创作的时候是以您个人为主宰,完全是您自己在创造这个世界,角色是如何转换的?
陈天铀:我反复认真地研读石涛画语录,石涛老师认为他学禅很差劲,但我们看石涛又感觉很神圣,不管从他的画语录所反映出来的艺术思想,还是他的艺术实践,都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禅宗对艺术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它实际上是对人的意识上的一种启迪作用,不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只是给你开一个门而已。读了有益,但你不能够死读它。从小我父亲教育我,读书一定要吃透精神,不要做书蠹,要像陶渊明的那种读书法:“好读书,不求甚解。”你读一本书,就有所收益。读书明理,读书是手段,明理才是目的。读书最终得转化成你自己的营养。不转化成自己的认识,天天人云亦云,读了也等于白读。
李书喜:您的文章,多次提到一个词,叫“圆览”,这是什么意思?
陈天铀:“圆览”就是整体性,对中国画来说是要融情理、物理、画理为一体。整体性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人的审美态度、价值趋向。《庄子》《列子》中有好多寓言故事,提出整体的认识,比方说庄子的浑沌说,浑沌以合和为貌,日凿一窍,七日而死。浑沌是一个整体,不能开窍,开窍就死了。庄子认为“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言。形形者无形。有些事情是需要整体把握的,你非要把它一点一点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把它具体到细节以后,结果整体不存在了,你也把握不了它了,你就落到细节的末梢里去了。所以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山水画的创作需要圆览的精神,就是整体把握。一切事物都是整体的,应该整体观照。王夫之说:“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焉。”孔子反复说:“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即整体把握的直觉式方法论,从一个中心逐渐展开,再回到中心汇合调整。虽然不断变化,但仍属于一个整体。中国的文化史、美术史也是这样。致广大,尽精微,致广大是主要的,你要有整体与通体的把握,在通体的把握过程中逐次展开,如一笔贯到千笔万笔,无非相生相让生出精微再回到整体,即千笔万笔还是一笔。如果你一开始就钻到细节里面去了,那么你往往会把整体丢掉。李可染先生谈画时候也这样说过,他认为一张画开始画的时候必须是整体把握,开始这张画我可以画出十个层次来,他吸收了好多素描的观念,对画有整体的把握,然后逐步地开始收拾收拾,就成了四五个层次,最后变成只有一两个层次,这张画他觉得就成功了,真正统一起来了。你去看,既整体又丰富,并不是非要拉开多少个层次,没有整体、没有一个混沌的感觉。画面是零乱的,所有有成就的大家,他的画都是通过圆览而统一的整体。
李书喜:这也就是您文章中提到的“持大象”。
陈天铀:对,贾又福先生也是这样,他反复强调一个词叫“浑沦”。“浑沦”这个词最早是龚贤提出来的,那么“浑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美学概念,就是龚贤在黑龚时期的那些画和贾又福先生的画,都是笔墨统一且整体的,每一笔落纸又是笔又是墨,又不是笔又不是墨,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就叫笔墨浑沦。用笔多少应该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都要做到笔墨浑沦。像八大山人那样,千笔万笔化成了一笔两笔,这是非常高超的,而黄宾虹先生满篇都是笔,千笔万笔本质上还是一笔,那也是非常高超的。这种辩证的关系他处理得比较好,所以贾又福先生抓住龚贤提出来的“浑沦”,要求他的学生注意笔墨“浑沦”。“浑沦”和“圆览”实际上在把握绘画的整体统一上是一致的。
六
李书喜:您提出过“立足本土,走向当代”的口号,您觉得这还需要什么条件?距离这些理想还有多远?
陈天铀:这是当时甘肃省美协主席莫建成先生提出来每个画家在画画的同时还要做点理论研究,并编辑了论文集。我就根据自己的创作结合全省的创作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我们当今的画家还得立足我们甘肃,不要好高骛远去看外面,外面的世界尽管很精彩,但是你与生活的本土是割不开的。
李书喜:我是这样理解“立足本土,走向当代”的,立足本土是您在甘肃深深地扎根进去,而走向当代就形成了您自己的一种风格,您认为当时是什么条件成就了您?
陈天铀:改革开放30多年来,艺术思想一直在不断解放。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是画家最好的时代,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所以有些人也批评我,说你搞的那些东西太保守,那没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的经历决定了我依然还是有那样一种追求,现在我不可能马上就变个现代派,追求西方最新的那些东西。我没有研究,我从感情上、从各个方面也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逐步地接触一些东西,这就是立足当代的意思,要跟上时代。石涛说过:“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人的东西不能安到你自己的身上去,你是当代人。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你的审美观念应该适应这个时代,如果一味地拟古,和宋画画的一样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不需要。你把自己的那种审美感受表达出来,就是你这个时代的东西。我们研究美术史,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实际上界限非常清晰,每个时期的画绝对不一样。贾又福先生有句话:“破执者悟,返法者迷。”你如果永远追根溯源的话,会把自己迷到那里面,而你迷到里面以后,就什么都创作不出来了。所以还是要向前走。
七
李书喜:黄宾虹说过“师古人”,那古人又师谁呢?从您的作品来看,您已经走出传统了。
陈天铀:传统它是个延续,有的人说传统是条河,各种支流加进来,有的人说传统像编一根绳子,最早古人用草就编起来了,后来用麻,再后来用尼龙、钢丝。反正这绳子一直在编,但每个阶段都不同。我们的追求是这样,实际上能做到什么,恐怕只有让后人去说。艺术家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不要想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自己把你自己搞得很“壮”,那实际上都没有意思。大家都很尊重贾又福先生,但他自己非常低调,根本不出来,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有些人特别张扬,成天在外面,好像要把自己提升到怎样的高度,实际上你什么都还不是。有些事情只能让别人去说,让后人去说。你自己把该做的事做好。
李书喜:时代很关键,不是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都有成就,您走到今天肯定是抓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君子居其实而不居其华”,在您眼中,什么是实,什么是华?
陈天铀:像贾先生那样,你认准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有自信心,不受别人的干扰,我想这实际上是一个毅力坚定的过程,有时候也的确想过不探索了。我从小喜欢画画,家里面是坚决反对的。小时候家里让我画画,是让我们画着玩一玩,不要到外面惹是生非去。长大后我父亲坚决反对我画画,因为他有一个堂哥,当时从北京艺专毕业以后,又到法国去学习,回来以后谁都看不上,自己也不画,最后把自己饿死了。所以我父亲特别害怕,认为画画的人搞不好会变成疯子,慢慢大了以后,家里就不让我画画了。但我已经喜欢上了,就偷着画一画,我也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爱好,慢慢地就走到这条道路上了,正如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真正喜爱这个东西,那种力量就非常大。中学时和我一起画画的同学有很多,我们在兰州市少年宫学画,当时张学乾老师做辅导员,那是在1962年到1963年。那个时候有好多人画得好,我都非常佩服。多少年过去了,有些人还在原地停留,没有多少进步。这大概是爱好加毅力的缘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善于学习很重要,不管是谁的东西,只要是你觉得好的,都应该去学,不要自我封闭。我和沈风涛一直在互相鼓励,因为我们俩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不像别人是艺术院校出来的,我们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而边玩边学的。但是有时候我也会疲劳,尤其是好长时间没有进步,也就觉得乏味没意思了。但我跑到他那里,看到他画的好多新东西,就觉得挺新鲜,就觉得那不行,还得画。他有时候不愿意画了,跑我这里来看到新东西,就又开始画了。所以说两个人互相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说,你在画画的过程中也要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互相砥砺,互相切磋,大家一块进步,要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估计够戗。
李书喜:你在《艺无止境勤探索》这篇文章中说:“中国绘画是从儒家、道家以及其后禅宗思想的作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画山非山。您多次去祁连山写生,十分了解和热爱祁连山,你是如何将眼中之山转化为心中之山的,让没有意识的自然之山变为您笔下的有灵魂的山?按照您的性格,您怎样去表现有灵魂的这种山呢?
陈天铀:禅宗反复强调,你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到最后见山还是山。这三个层次是个逐步升华的过程,对一个自然的山,你的精神折射到山,山的精神折射到你。那山的精神是什么呢?山的精神是你赋予它的,山的精神是你赋予它的认识和理解,在你的感觉中这山是雄伟、险峻、挺拔的还是秀丽隽美的,是孤寂的还是热烈的,是恬静的还是跃动的,你就给它赋予了某种品格,这种东西又反过来影响你,正像《易经》中所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物我通达,借助洞察天地万物且能与物产生精神感应。这种精神上的敏感度愈具体、愈强烈、愈深刻,表达出来才能愈感人。这中间就是自然与“我”反复沟通的过程。中国画强调意象思维,从具体的情境中由象及意,得意忘象,也就是何海霞先生提出的写生中目识心记的过程,你得用心去体会,你在反复的体会中,才能产生一种感情那样的东西。一句话,真正的自由、自我、真性情才是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八
李书喜:您认为祁连山的灵魂是什么?
陈天铀:我觉得祁连山作为自然形态的山,它和青藏高原上的很多山脉是一样的。和其他地方的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终年积雪的,上面是雪山,中间是一种荒漠式的形态,最下面随地段的不同,有些是草甸,有些是森林。从地质学上说,祁连山是古海,最后地壳挤压形成了现在的祁连山形态。相对来说,祁连山是个比较新的山脉,和它北面的马鬃山不太一样,那是个比较古老的山脉,已经崩塌垮掉了。河西走廊是以祁连山为主的,就中国西部而言,河西走廊起的作用非常大,成为人类在此生存、居住、繁衍、发展的一个环境,几十个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争战、融合。同时这里不单有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还有世界文化,印度犍陀罗、东罗马等的文化风格在这里交流、融合,体现出仁爱、和谐、发展、进步的特点。所以你要从它的自然形态、地质形态一直到历史文化形态来理解。我觉得祁连山是养育甘肃的母亲山,充满了慈祥和仁爱。祁连山有些地方非常险峻,有些地方又很不起眼,它是多面的,既有壮阔的一面,也有柔情的一面,所以在画它的时候就应该把它不同的面都表现出来,表现这种心中的山。这个认识是一种不断升华的过程,你第一次看那是个自然形态的山,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你再带着感情去画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把它好的那一方面表现出来,充分一些,有些不需要的东西就可以删减掉,去找表现它的一些语言。中国画离不开笔墨,离不开线,这里面你要找到合适的用笔、用墨,还有线,在反复的锤炼过程中寻找。每个人心目中有每个人的认识,我的表现还是不够完善,还要进一步地认识它,表现它多面的形态,特别是要表现出祁连山的精神内涵。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它。
李书喜:您想通过祁连山表达您怎样的思想?
陈天铀: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甘肃和青海沿祁连山一线,都是受惠于祁连山的,所以这个地方的人都把它当作神山。在画的过程中,我觉得甘肃地貌和大中国来说很像,喜马拉雅山在中国的西南面,祁连山在甘肃的西南面,可以说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就没有河西的这几块绿洲。而酒泉、张掖和武威这三个大的绿洲的形成,全依赖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千万年祁连山的养育,才有了丝绸之路的繁盛,也才有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这几种文化综合起来的这座山,实际上是我们甘肃人,乃至西部人精神上的一种象征,是造福这块地方的。在表现它的过程当中,要注入这种文化。中国艺术崇尚直指人心的精神美,画祁连山必须有高尚精神的投入。
九
李书喜:您在多篇文章当中都提到过石鲁,他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如何看待他的?
陈天铀:石鲁是我精神上的导师,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精神上的榜样。石鲁先生的画论和画对我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思想非常活跃的人,还写过电影剧本,版画又搞得那么好,后来转到中国画,他很快就能够抓住很精髓的东西,直接抓住中国画最要害的几点东西,书法上也是直接抓住最要害的东西,思想活跃,不断地在考虑问题,不断地在探索各种各样的东西,像这样的人特别少。我们说长安画派,有些人强调赵望云先生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没有石鲁就绝对没有长安画派,应该说他是真正的核心,因为他的艺术思想决定了长安画派的高度。何海霞先生在其回忆长安画派创作时曾说:“石鲁是长安画派群体中真正的核心。”何先生的绘画之路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他在北京琉璃厂靠自己卖画的阶段,当时就是一种求生手段,跟随张大千以后眼界打开了,对传统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何先生到陕西,接触了石鲁先生以后,石鲁把他调到陕西美协,他那个时候在西安市卫生局给人家画卫生宣传画,画讲究卫生、计划生育那些东西,调入陕西美协创作小组后他接受了石鲁的好多思想,在石鲁和赵望云的影响下,他了解到中国画还可以这样画。我开玩笑说,张大千的画很好,但怎么都有一种脂粉气,而何海霞的画真的有一股豪气在里面,有那种豪迈的大丈夫气概,但从里面的结构看,都有李成的笔意、有张大千一样的笔法结构。同样是张大千的结构,他本人的依然有一种媚气,那种很柔美的东西,而何先生却是一种正气、豪气。他们在气息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何海霞说这就是石鲁对他的影响。真正下去到陕南、陕北农村去写生,突然用传统的笔墨语言来表达这种当代的现实生活,一下子打开了他的思路,所以何海霞先生的画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脱开了原来张大千先生对他的那种束缚。他有张大千的影子,但他已经完全不是张大千了,是何海霞自己的。能够达到这个层面,他特别感谢石鲁。石鲁对他精神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石鲁比何海霞小,何先生说,石鲁当时对他们这些艺术家特别尊重,他始终把赵望云推到前面,赵望云强调用中国画写生,这也是先行一步的,但是真正从艺术思想来说,触角所能达到的高度广度,特别是艺术精神上的高度,还是以石鲁先生为核心的,没有石鲁,长安画派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长安画派必须要把石鲁吃透,他的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是最高的。1963年前后,很多人在谈论长安画派的时候,说石鲁的画前不见刘、李、马、夏,后不见“四王”、吴、恽,是“野、怪、狂、黑”。1963年到1964年那时候美术杂志集中对石鲁的画争论了一段时间,当时双方论战的文章相当激烈,但是后来石鲁立住了,作品成了时代的经典之作。为什么要跟“四王”、吴、恽一样呢?为什么要和刘、李、马、夏一样呢?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艺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都决定了石鲁的确是一位大师,对整个西北乃至全国来说,不论是现在还是今后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十
李书喜:所以吴冠中先生说徐悲鸿是“美盲”,说石鲁是日本三山”,不如中国的一块“石头”。
陈天铀:的确是这样。他非常开放,他早期从版画开始,到后来和赵望云先生的埃及写生那批画,在那个时候来说,中国画家到现场写生,画到那样的程度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
李书喜:陈伯希先生说您的画是敦煌画派的基础之一,您是如何看待敦煌画派的?本土画家应该如何走出甘肃?
陈天铀:一个画派应该是一个美术现象的总结,它是一批人共同的审美追求,组成一个相近的、表现一定特点的成功的美术团体。是后人把他们总结的,你不能在此之前先把自己归到哪个画派,这就本末倒置了。画派的形成是后人总结的东西,对每个画派的人来说,你做好自己的事,剩下的事情是别人去说的,是后人说的。但对具体的某一地方来说,还是需要将地方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的,不能陷到地方性里头去,因为地方性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糟粕,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但是这里面也有好的东西,原生态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区别它,就是它必须符合全人类审美的一种共同追求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个高度、广度去谈地域性,实际上也是谈不起来的,这是要辨证地来看的。
做地域性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普遍性的审美价值取向,要对地域性的东西有一个去伪存真、汲取精华、去糟粕的过程。要去掉一些简单的东西,去求得一些精彩的东西。对画派而言,每个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定好以后,坚持走下去,至于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个人的素质、年龄、阅历、健康等各种因素可能都会有所限制。比如说石鲁,如果说石鲁没有过早去世,他的那种精神能够真正得到全面的发扬,他的影响还会更大。现在陕西的这些画家里面,像崔振宽、王金岭、王炎林、方鄂秦、张之光、苗墨、李世南、王西京、徐义生,他们当时很多都是受他直接影响的。也就是说,陕西现在中坚派力量都是在石鲁精神的培育和教导下成长的。他们发挥出来了,有了各自的成就。甘肃没有这种榜样,无法跟陕西比。这批人应该要好好感谢石鲁,因为他们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没有不受益于石鲁的,整个长安画派后续的这些人,如果能够继承石鲁的那种思想,能够真正把长安画派的精神延续下去,应该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石鲁的过早去世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
李书喜:最近您在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新想法、新动作?
陈天铀:怎么样把敦煌的文化精神、敦煌的艺术高度,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和梳理,我有自己的想法。在分析研究中汲取精华,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补充和完善。应该重视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文化代表了世界上几个大的重要文明汇聚的观点。在这个汇聚融合的过程中,敦煌的精神就应该是中华文化怎样立足本土、开放胸襟,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地丰富自己。而这种精神是需要延续的,要把这种敦煌文化精神和具体的敦煌画派的操作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去做工作。
李书喜:怎样理清学术敦煌和地域敦煌?
陈天铀:将敦煌作为一种显学去研究,就是认识到它是人类精神文化财富,对后世有指导意义。我们学习敦煌艺术,要从精神高度上把握。如果仅仅去莫高窟临摹一些壁画或是把那种历史现象画一画,那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工作。像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反复在丝绸之路走,深入地考查历史、文化,并采风、写生。他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在精神上的追求非常高。我们应该吸收一下这些东西,不要太局限具体的敦煌,要从大丝绸之路去考查研究。所以我认为,谈敦煌文化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离不开丝绸之路的研究。这些年想法很多,但实际上都做不到,我想着静下来,一方面总结一些东西,一方面再把思想梳理一下,再思考对艺术精神、艺术语言的研究和锤炼,还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像历代前贤那样,皓首穷年,不敢荒嘻。
版权声明
为加强原创内容保护,日前,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各子报、甘肃新媒体集团各平台已将其所有的版权统一授予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维权及给第三方的授权许可。即日起,上述媒体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刊登的,包括文字、图片、摄影、视频、音频等原创作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以及H5、海报、AR、VR、手绘、沙画、图解等新媒体产品,任何机构、媒体及自媒体未经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许可,不得转载、修改、摘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并传播上述作品。
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致电0931-8159799。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
相关新闻
- 2020年12月10日创作谈 ▏传承创新 融铸西北心像——大西北山水画笔墨语言的传承创新与当下创作实践的思考
- 2020年11月18日【名家·文学·雪漠】武魂与疼痛——《凉州词》创作谈
- 2020年09月27日创作谈 ▏何 鄂《再回首》